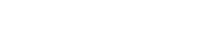分類目錄
CATEGORIES
-
主要課程
- 2006《略論》奢摩他
- 2007加行六法
- 2007四聖諦初探
- 2007道次第實修綱要
- 2008前後世
- 2008業果
- 2008道次第概說
- 2008依師軌理
- 2008四聖諦再探
- 2009隨念佛功德
- 2010大乘不共四聖諦
- 2011宗義-外道與毗婆沙宗
- 2012道次第抉擇與辨析
- 2012功德之本頌
- 2013慈愛的實修
- 2014釋量論第二品
- 2015中觀見地
- 2016緣起見無害行
- 2016《現觀》四聖諦
- 2016三主要道
- 2017如意牟尼夢語
- 2017四法印(汪傑格西)
- 2017四法印(悲桑格西)
- 2017《略論》與道次第實修(上)
- 2018《略論》與道次第實修(下)
- 2018空性概說
- 2019父母瑜伽
- 2022空性自習指導
- 2023給病中的你
- 開示彙編
- 主題釋疑
- 請問悲桑老師
- 請法團析釋
- 經論選讀
- 好文選讀
- 演講、談話與請益集
第16課【修止正行】心住所緣之時:修止所緣(三)
【原文】特欲成辦具相之止,未修成前,不可多換異類所緣;因多更換異類所緣修三摩地,反成修止最大阻礙。聖者馬鳴論師說云:「應於一所緣,堅固其意心,若易多所緣,煩惱擾其意。」《道炬論》中亦云:「任於一所緣,令意住善法。」說「於一」者,是指定詞。
觀修佛身像可以累積很大的福德,而且,對佛的身等功德思惟得愈多,就會對佛生起愈強的信心;一旦生起信心,便會生起想要跟他一樣的希求心,這種希求就是非常珍貴重要的菩提欲求。接著你會想,光想著自利根本不可能達成目標,要變得跟佛一樣,唯一的方法是利他,因而影響你想要利他的心。由此可知,以佛像為修止所緣有很多好處,就算沒有成辦奢摩他,也會使得心變得更穩定。
不過,若是在專修止的階段,暫時上來說,就只專注在要修的所緣,其他的都不要多想,甚至其他的善行也都要暫時放下。例如,當你決定現階段要全力修止,並打算完整地獲得修止的成就,連講經說法等事情都要暫停,更別說是更換所緣,這是根本不可以做的事。若你眼前並沒有打算要專心修止,而是為了集福德、或是為了讓心變得更堅穩些而修,則你可以在白天做別的善行,晚上撥時間修止;若你現階段以修止為主要目標,就不可以兼做別的事情,就算是善行也要暫時放下,否則很難修出結果來。別的不談,專修止的期間,連在座間也要憶念所緣,心的力道依舊要放在所緣境上。
總之,若經常更換所緣境,沒辦法修成止。文中接著列舉這種作法的根據,馬鳴論師說:「應該選擇一個所緣,設法使心穩固地安住其上;若經常更換所緣,心會無法安住。」此外,《道炬論》也說:「雖然一般而言所緣境非常多,但是在修止的時候,應該選擇一個去修就好。」這些論典都說不應該更換所緣。
【原文】初於心獲得所緣之量:依次觀想頭部、雙手、身體餘分及二足相數次,其後作意身之總相,若能於心現起半分粗略肢體之相,縱無清晰具光明相,亦應以此為足,於彼攝心;若不以此為足而攝其心,反求較前清晰之相而數觀想,所緣雖可略為清晰,然此非僅不得堅固妙三摩地,反成得三摩地之障。所緣雖不甚顯,然若能於半分攝持其心,則能速得妙三摩地;次若欲令更為清晰,則見功效,故易成辦明分。此乃出自智軍論師所著教授,極為重要。
這段文談的是剛開始修的時候,如何可以算是「確定了所緣」。心裡觀想著:這是頭、這是雙臂、這是身體、這是雙足、這是坐姿……如此反覆做幾次,心裡會顯現出所緣的義共相。當義共相顯現時,不必再像剛才那樣想,只要把心安住其上就好;否則,若繼續想著「這是頭、這是手……」,心又會開始去觀察,此時心又會受到影響。之前做的那些「這是頭、這是手」等觀察,是為了把所緣境顯現出來;所緣境顯現了,就要把心安住其上。
若心可以粗略地顯現出所緣境,即便不很清楚也沒關係,就要開始以這樣的所緣境去練習。例如,雖然理論上應該把心中顯現的佛視為真佛,但一開始做不到沒關係,即便顯現出來的只是一個很粗分的影像,都應先以此為滿足,不要想馬上要做得很好,應該設法讓心安住在已經觀想起來的所緣境上。
「若不以此為足而攝其心,反求較前清晰之相而數觀想,所緣雖可略為清晰,然此非僅不得堅固妙三摩地,反成得三摩地之障。」這段話的意思是,在初修時,若要求自己把所緣境明顯地觀想起來,就必須一再觀想。這樣做雖然的確有助於所緣境變得明顯,但會使你的心不易安住,反而成為得定的障礙。「所緣雖不甚顯,然若能於半分攝持其心,則能速得妙三摩地;次若欲令更為清晰,則見功效,故易成辦明分。」若在所緣境僅有粗分顯現時就去練習,設法安住於這個境上,會較快得到住分。在住分稍微穩定一些時,再去思惟所緣境的細部相貌,此時所緣境就會更清楚些。
總之,不要急著把所緣境觀想到很清楚。即使一開始不太清楚也沒關係,就依於已現起的所緣境,設法讓心能安住其上,反覆如此練習。這是從智軍論師傳下來的教授,它很重要。這是初學者在最開始時一定要知道的事。先透過幾次逐步思惟「這是頭、手……」的方式,讓心中現起所緣境,一旦概略地現起所緣境,就不再做觀察,不要再設法讓它變得更清晰,要先設法讓心可以安住在已有的所緣境上。
此處講的觀察,與我們平常講的觀察修是一樣的,它並不是思惟是非有無,例如觀察有沒有前後世等,而是針對已在心中顯現的所緣,以佛像來說,隨著已經顯現的行相去想「這是佛的眼睛,這是佛的雙臂」,這樣就是在觀察了。由此可知,它與抉擇是非有無的觀察方法不一樣。這裡說的是,當內心已經顯現粗分的所緣境後,就不要再繼續觀察,針對內心已經顯現的所緣境,設法讓心不動地安住其上,不觀察、止住就好,此即所謂的「止住修」。以佛像為例,先去思惟佛的身像,讓他的行相在心中現起,接著就把心安住其上。
不過,上述這些話,若你自己沒有真正做過,恐怕很難對這段話有概念;若這樣去修過,講到「安住」二字,雖然你還做不到,但已經可以體會它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。與修三摩地相關的內容很多都是這樣,若你根本沒實修過,則別人再怎麼講,你還是不懂真正的意思;若有實修,雖然沒有修出結果,但你至少懂得那些文字到底在說什麼。所以,至少花幾天努力照著書上說的方法實修,你當然不可能在幾天之內就修出什麼結果,但在實修後再次把書拿出來讀,才會真正懂得書裡在講什麼。否則,你知道的只會是朦朧模糊的概念,無法準確地懂得真正的內容。
【原文】現所緣境時,即緣身之總相,若身一分清晰顯現,則可緣彼;若彼復沒,仍緣總相。爾時,若欲修黃然現紅等「顏色不定」,或欲修坐然現立等「外形不定」,或欲修一然現二等「數量不定」,或欲修大然現小等「大小不定」,不可隨彼等相而轉,應以根本所緣為所緣境。
「身之總相」的意思是在心中形成概略的粗分行相,一個頭、兩隻手、結跏跌坐,只要心中顯現出了這樣的行相,就讓心安住其上;「若身一分清晰顯現,則可緣彼;若彼復沒,仍緣總相」的意思是,若同時可以明顯地現起身體的某個部份,就以「整體模糊、部份清楚」的行相為所緣去修。例如整體的佛像粗略模糊,但是佛的手可以清楚顯現,就以「在總體模糊的基礎下,加上清楚的手」為所緣去修。若這清楚的手漸漸又變得模糊,就以本來已生起的粗分整體的佛身像為所緣去修。
然而,若本來打算修的佛身像是黃色,在修的時候卻現起紅色或其他顏色的身像,那時不要讓心跟隨這些顯現去想;同樣地,你本來打算修的佛身像的姿勢是結跏趺坐姿,但在修的時候卻現起站姿或走動的佛身像,此時不要讓心隨之而轉。就像這樣,無論數量、大小等,若出現與本來設定不合的顯現時,都不應該讓心跟著這些顯現去修,應該只隨著本來設定的所緣境行相去修。
※ 重點整理:
觀修佛身像可以累積很大的福德,而且,對佛的身等功德思惟得愈多,就會對佛生起愈強的信心;一旦生起信心,便會生起想要跟他一樣的希求心,這種希求就是非常珍貴重要的菩提欲求。接著你會想,光想著自利根本不可能達成目標,要變得跟佛一樣,唯一的方法是利他,因而影響你想要利他的心。由此可知,以佛像為修止所緣有很多好處,就算沒有成辦奢摩他,也會使得心變得更穩定。
不過,若是在專修止的階段,暫時上來說,就只專注在要修的所緣,其他的都不要多想,甚至其他的善行也都要暫時放下。例如,當你決定現階段要全力修止,並打算完整地獲得修止的成就,連講經說法等事情都要暫停,更別說是更換所緣,這是根本不可以做的事。若你眼前並沒有打算要專心修止,而是為了集福德、或是為了讓心變得更堅穩些而修,則你可以在白天做別的善行,晚上撥時間修止;若你現階段以修止為主要目標,就不可以兼做別的事情,就算是善行也要暫時放下,否則很難修出結果來。別的不談,專修止的期間,連在座間也要憶念所緣,心的力道依舊要放在所緣境上。
總之,若經常更換所緣境,沒辦法修成止。文中接著列舉這種作法的根據,馬鳴論師說:「應該選擇一個所緣,設法使心穩固地安住其上;若經常更換所緣,心會無法安住。」此外,《道炬論》也說:「雖然一般而言所緣境非常多,但是在修止的時候,應該選擇一個去修就好。」這些論典都說不應該更換所緣。
【原文】初於心獲得所緣之量:依次觀想頭部、雙手、身體餘分及二足相數次,其後作意身之總相,若能於心現起半分粗略肢體之相,縱無清晰具光明相,亦應以此為足,於彼攝心;若不以此為足而攝其心,反求較前清晰之相而數觀想,所緣雖可略為清晰,然此非僅不得堅固妙三摩地,反成得三摩地之障。所緣雖不甚顯,然若能於半分攝持其心,則能速得妙三摩地;次若欲令更為清晰,則見功效,故易成辦明分。此乃出自智軍論師所著教授,極為重要。
這段文談的是剛開始修的時候,如何可以算是「確定了所緣」。心裡觀想著:這是頭、這是雙臂、這是身體、這是雙足、這是坐姿……如此反覆做幾次,心裡會顯現出所緣的義共相。當義共相顯現時,不必再像剛才那樣想,只要把心安住其上就好;否則,若繼續想著「這是頭、這是手……」,心又會開始去觀察,此時心又會受到影響。之前做的那些「這是頭、這是手」等觀察,是為了把所緣境顯現出來;所緣境顯現了,就要把心安住其上。
若心可以粗略地顯現出所緣境,即便不很清楚也沒關係,就要開始以這樣的所緣境去練習。例如,雖然理論上應該把心中顯現的佛視為真佛,但一開始做不到沒關係,即便顯現出來的只是一個很粗分的影像,都應先以此為滿足,不要想馬上要做得很好,應該設法讓心安住在已經觀想起來的所緣境上。
「若不以此為足而攝其心,反求較前清晰之相而數觀想,所緣雖可略為清晰,然此非僅不得堅固妙三摩地,反成得三摩地之障。」這段話的意思是,在初修時,若要求自己把所緣境明顯地觀想起來,就必須一再觀想。這樣做雖然的確有助於所緣境變得明顯,但會使你的心不易安住,反而成為得定的障礙。「所緣雖不甚顯,然若能於半分攝持其心,則能速得妙三摩地;次若欲令更為清晰,則見功效,故易成辦明分。」若在所緣境僅有粗分顯現時就去練習,設法安住於這個境上,會較快得到住分。在住分稍微穩定一些時,再去思惟所緣境的細部相貌,此時所緣境就會更清楚些。
總之,不要急著把所緣境觀想到很清楚。即使一開始不太清楚也沒關係,就依於已現起的所緣境,設法讓心能安住其上,反覆如此練習。這是從智軍論師傳下來的教授,它很重要。這是初學者在最開始時一定要知道的事。先透過幾次逐步思惟「這是頭、手……」的方式,讓心中現起所緣境,一旦概略地現起所緣境,就不再做觀察,不要再設法讓它變得更清晰,要先設法讓心可以安住在已有的所緣境上。
此處講的觀察,與我們平常講的觀察修是一樣的,它並不是思惟是非有無,例如觀察有沒有前後世等,而是針對已在心中顯現的所緣,以佛像來說,隨著已經顯現的行相去想「這是佛的眼睛,這是佛的雙臂」,這樣就是在觀察了。由此可知,它與抉擇是非有無的觀察方法不一樣。這裡說的是,當內心已經顯現粗分的所緣境後,就不要再繼續觀察,針對內心已經顯現的所緣境,設法讓心不動地安住其上,不觀察、止住就好,此即所謂的「止住修」。以佛像為例,先去思惟佛的身像,讓他的行相在心中現起,接著就把心安住其上。
不過,上述這些話,若你自己沒有真正做過,恐怕很難對這段話有概念;若這樣去修過,講到「安住」二字,雖然你還做不到,但已經可以體會它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。與修三摩地相關的內容很多都是這樣,若你根本沒實修過,則別人再怎麼講,你還是不懂真正的意思;若有實修,雖然沒有修出結果,但你至少懂得那些文字到底在說什麼。所以,至少花幾天努力照著書上說的方法實修,你當然不可能在幾天之內就修出什麼結果,但在實修後再次把書拿出來讀,才會真正懂得書裡在講什麼。否則,你知道的只會是朦朧模糊的概念,無法準確地懂得真正的內容。
【原文】現所緣境時,即緣身之總相,若身一分清晰顯現,則可緣彼;若彼復沒,仍緣總相。爾時,若欲修黃然現紅等「顏色不定」,或欲修坐然現立等「外形不定」,或欲修一然現二等「數量不定」,或欲修大然現小等「大小不定」,不可隨彼等相而轉,應以根本所緣為所緣境。
「身之總相」的意思是在心中形成概略的粗分行相,一個頭、兩隻手、結跏跌坐,只要心中顯現出了這樣的行相,就讓心安住其上;「若身一分清晰顯現,則可緣彼;若彼復沒,仍緣總相」的意思是,若同時可以明顯地現起身體的某個部份,就以「整體模糊、部份清楚」的行相為所緣去修。例如整體的佛像粗略模糊,但是佛的手可以清楚顯現,就以「在總體模糊的基礎下,加上清楚的手」為所緣去修。若這清楚的手漸漸又變得模糊,就以本來已生起的粗分整體的佛身像為所緣去修。
然而,若本來打算修的佛身像是黃色,在修的時候卻現起紅色或其他顏色的身像,那時不要讓心跟隨這些顯現去想;同樣地,你本來打算修的佛身像的姿勢是結跏趺坐姿,但在修的時候卻現起站姿或走動的佛身像,此時不要讓心隨之而轉。就像這樣,無論數量、大小等,若出現與本來設定不合的顯現時,都不應該讓心跟著這些顯現去修,應該只隨著本來設定的所緣境行相去修。
※ 重點整理:
- 專修止時不可更換所緣,這是修止的關鍵。如馬鳴論師所說,應在單一所緣上使心安住,頻繁更換會成為最大障礙。專修期間,甚至其他善行也需暫時放下。
- 以佛像為所緣雖有諸多利益(如累積福德、增長信心),但在專修階段應單純專注於修止,不應分心思考其他功德。
- 初修時確立所緣的方法是:先觀想頭、手等各部分數次,待形成粗略整體印象後,即應以此為足,著重於心的安住,而非追求更清晰的影像。
- 過分追求所緣清晰反成障礙。智軍論師強調:即使所緣不甚明顯,若能令心安住,反而更易成就三摩地;待心安住後,清晰度自然增進。
- 當所緣顯現與原定不符時(如顏色、姿勢、數量、大小有異),不應隨之轉變,應堅持回到最初確立的所緣。若某部分特別清晰,可以接受,但若又模糊,則回歸整體。